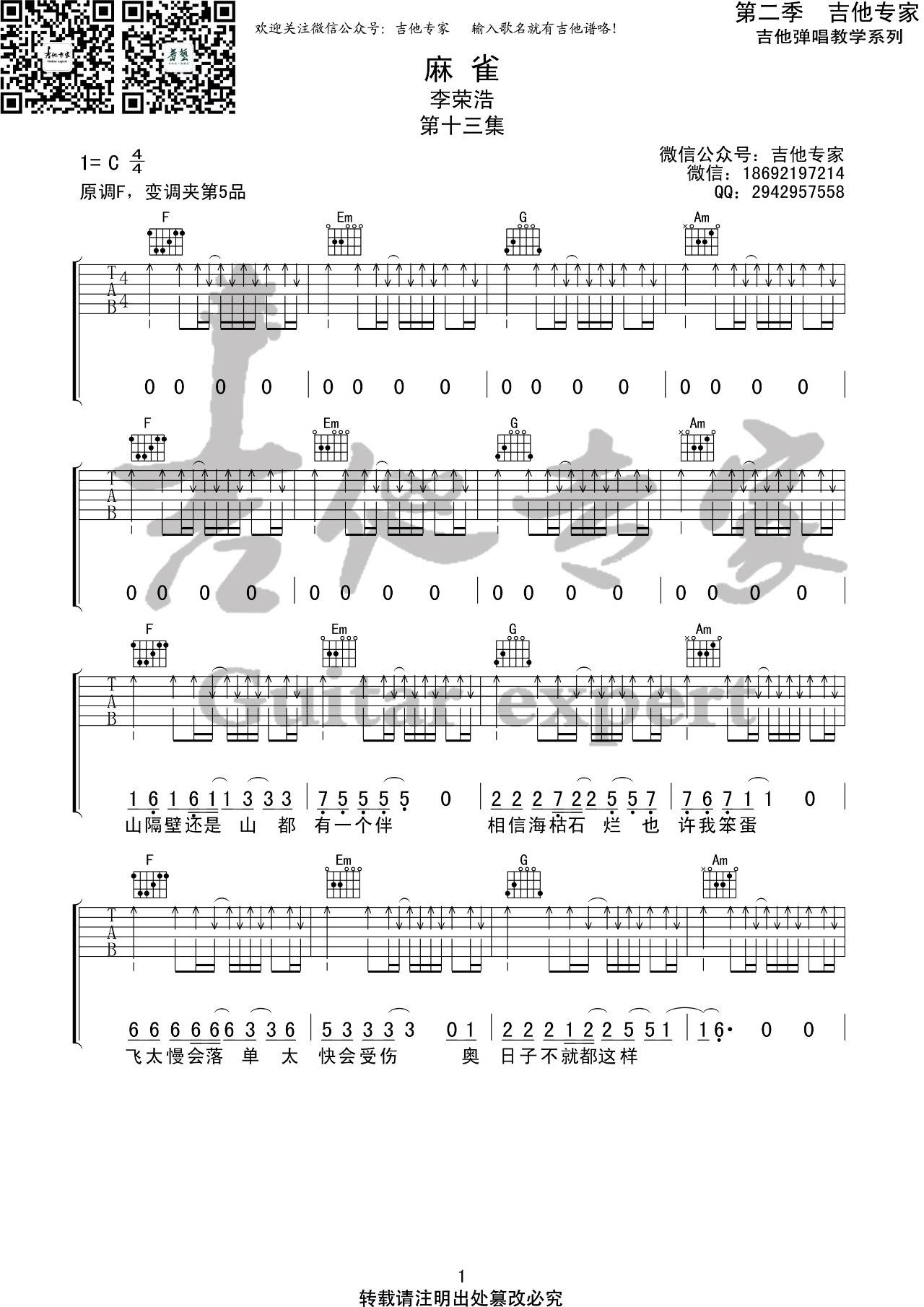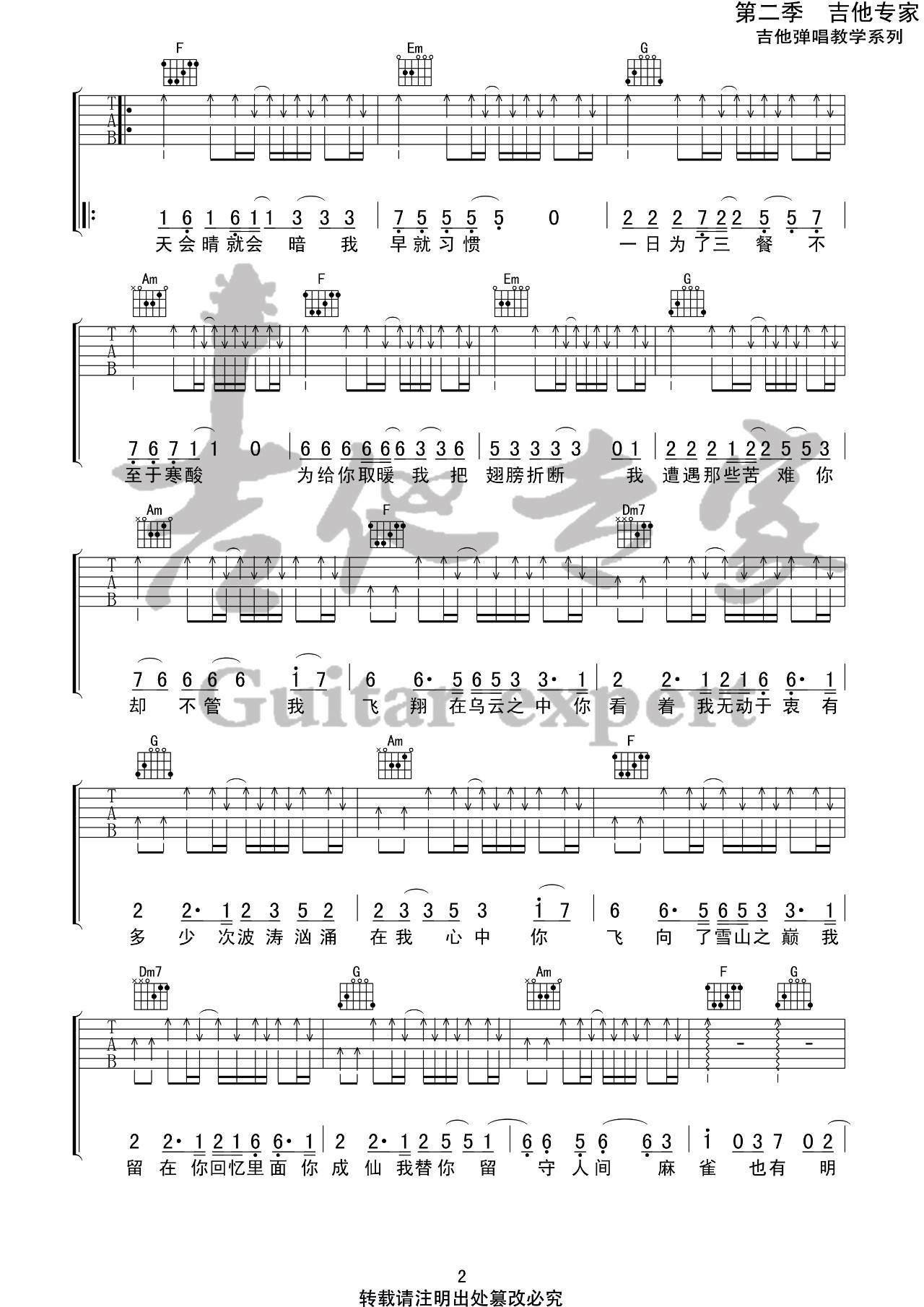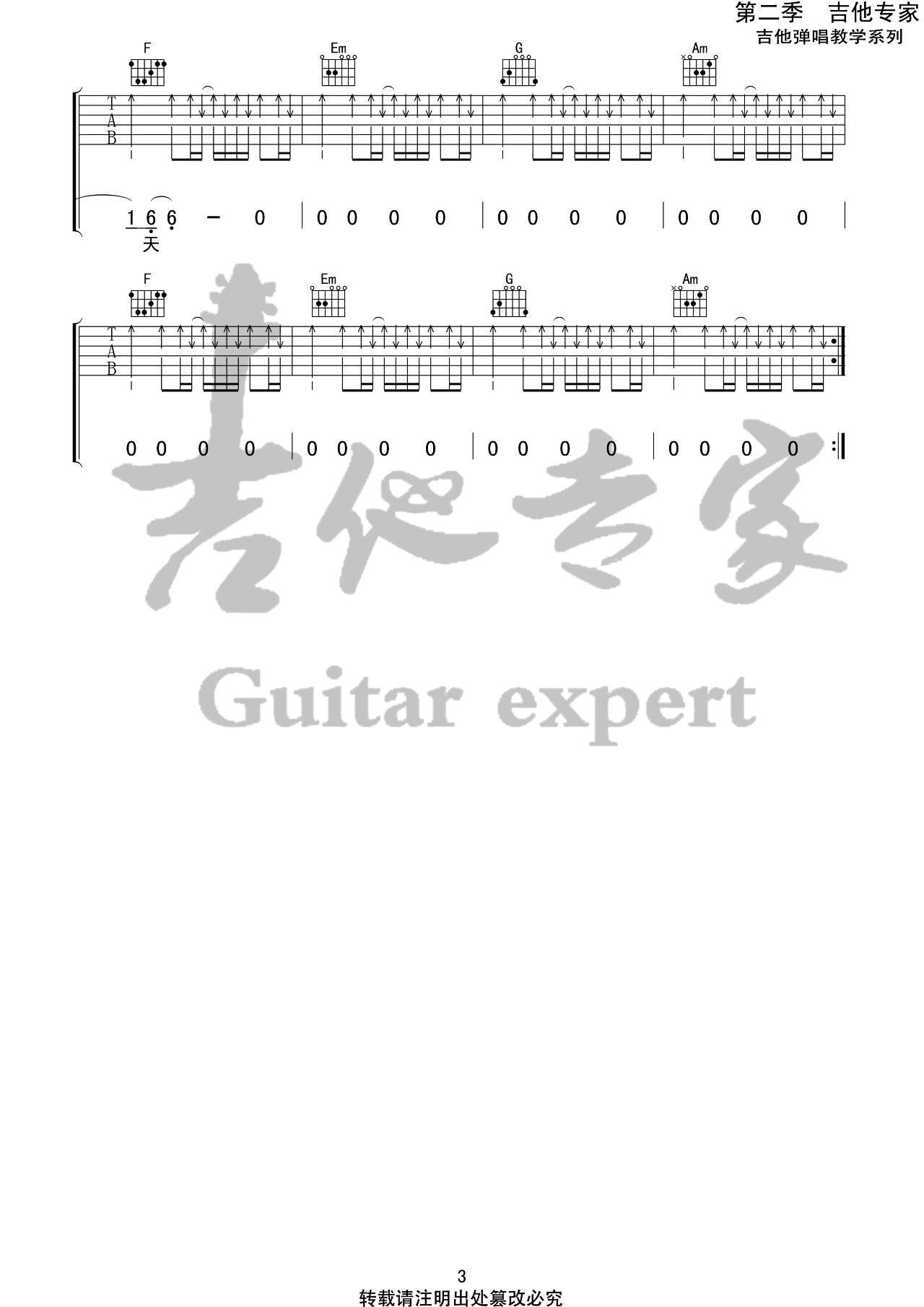《麻雀》以朴素意象构筑都市生活的生存寓言,羽毛沾着霓虹的鸟雀成为现代人精神困境的隐喻载体。钢筋森林的棱角划破传统田园牧歌,电线杆上的守望者用喙叩击着存在主义的命题。歌词中反复出现的"振翅"动作暗含西西弗斯式的抗争哲学,渺小生物在玻璃幕墙间的每一次起飞,都是对城市化生存法则的温柔反抗。晨光与暮色交替的叙事结构,揭示当代劳动者循环往复的生命状态,而"叼着面包屑穿越风雨"的具象描写,将物质追求与精神漂泊并置于同一生存平面。那些被尾气熏黑的羽毛,实则是异化劳动在肉体留下的诗意印记。副歌部分不断强化的"低飞"意象,构成对高空霸权话语的消解,在贴地飞行中重新发现生存的尊严。看似描写鸟群迁徙的生态图景,实则勾勒出城市化进程中人的精神流放史,水泥缝隙里生长的野草与排水管凝结的露珠,共同拼凑成残缺的生存美学。当麻雀成为都市文明的共栖者,它们的啾鸣便成了物化时代的安魂曲,在机械轰鸣的间隙里保存着未被驯服的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