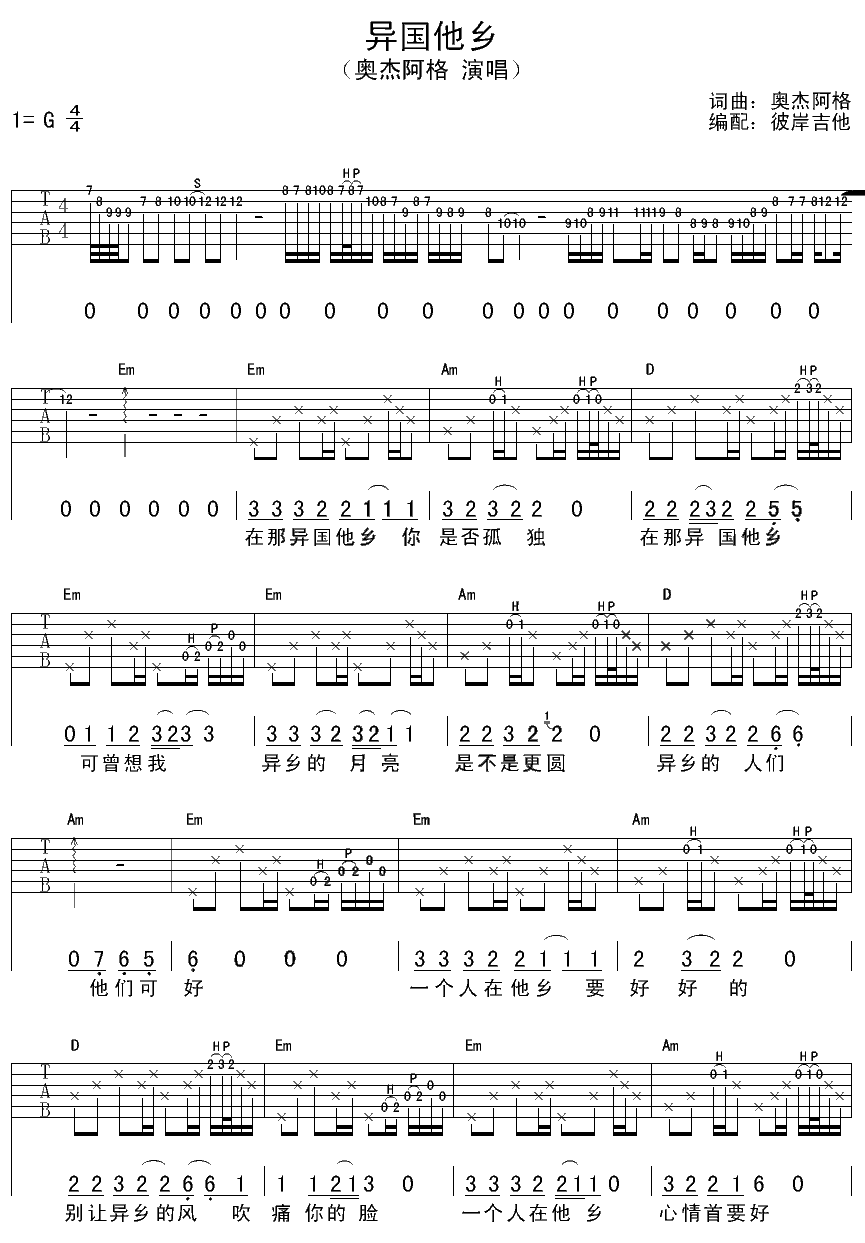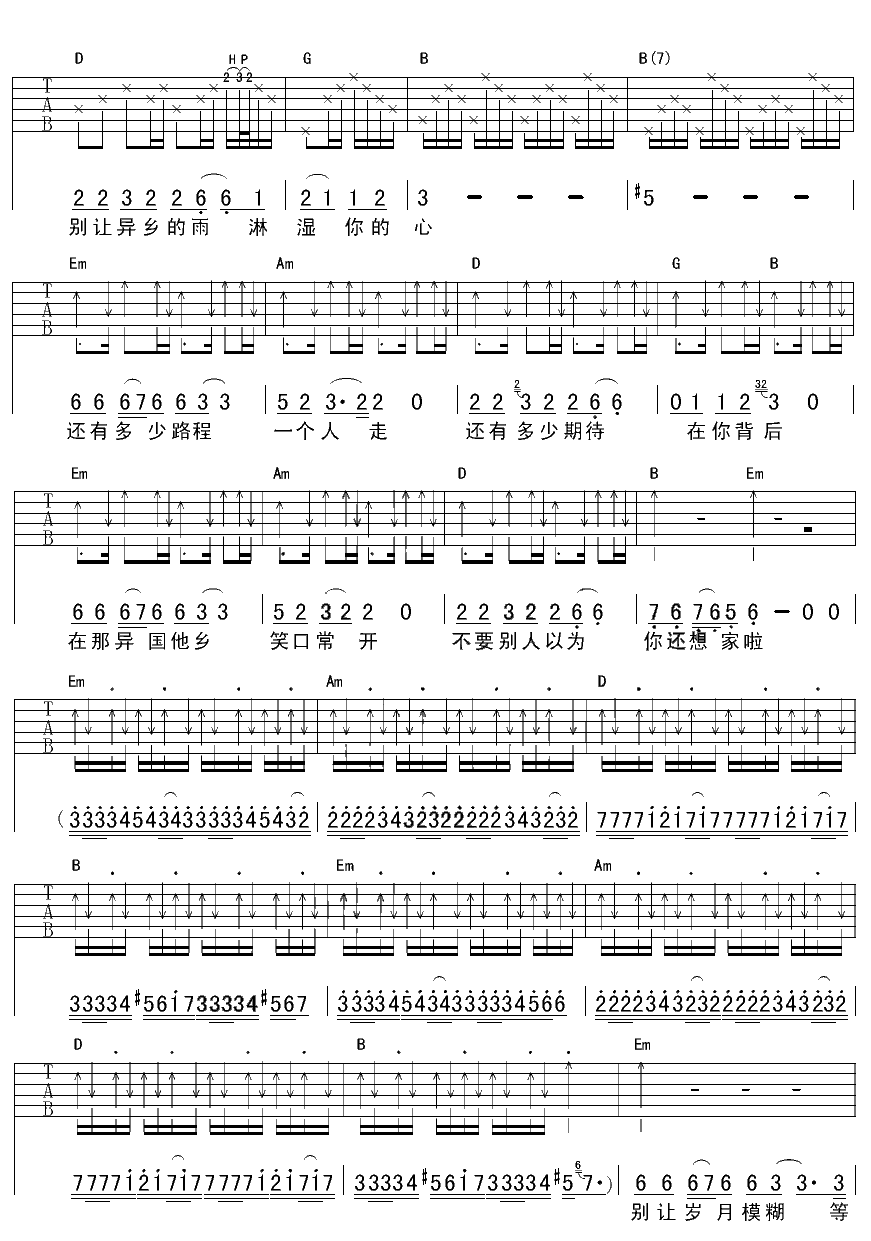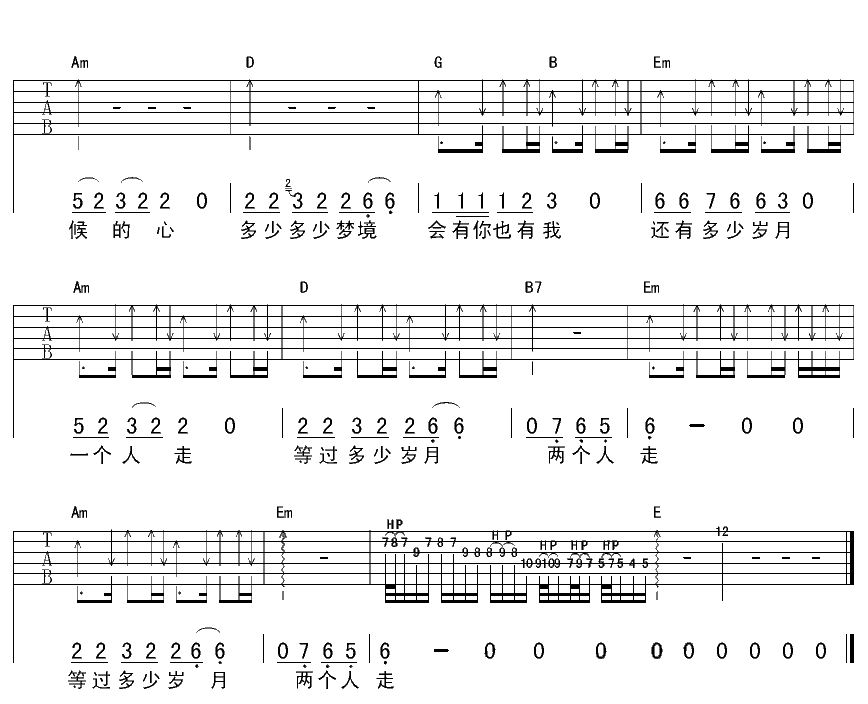《异国他乡》以漂泊者的双重视角展开,既描摹地理坐标的疏离感,更深入精神家园的追寻轨迹。歌词中反复出现的行李箱、陌生街灯等意象,构成流动的现代人生活图鉴,金属拉杆轮摩擦地面的声响成为当代游牧民族的独特韵脚。这种迁徙并非浪漫的冒险,而是带着时差与季风在血脉里沉淀的钝痛,便利店微波炉加热的便当与故乡灶台炊烟形成味觉记忆的残酷对照。歌词巧妙运用气候符号作为情感载体,赤道暴雨与北国雪原的极端气候隐喻文化休克的两极,而晾衣绳上冻结的衬衫则具象化异乡人难以晾干的乡愁。第二段主歌出现的方言电话片段,揭示数字时代下亲密关系的畸变——电磁波传递的母语在跨国电缆中不断衰减,最终成为失真的电子杂音。副歌部分不断强化的"经纬度眩晕",实则是全球化时代个体的普遍生存困境,当GPS能精准定位每栋公寓却无法标注心灵坐标,这种科技与情感的悖论成为当代漂流者的集体病症。结尾处突然插入的童年童谣旋律残片,构成时空折叠的听觉蒙太奇,暗示无论跨越多少时区,某些记忆频率始终在潜意识深处持续发射着微弱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