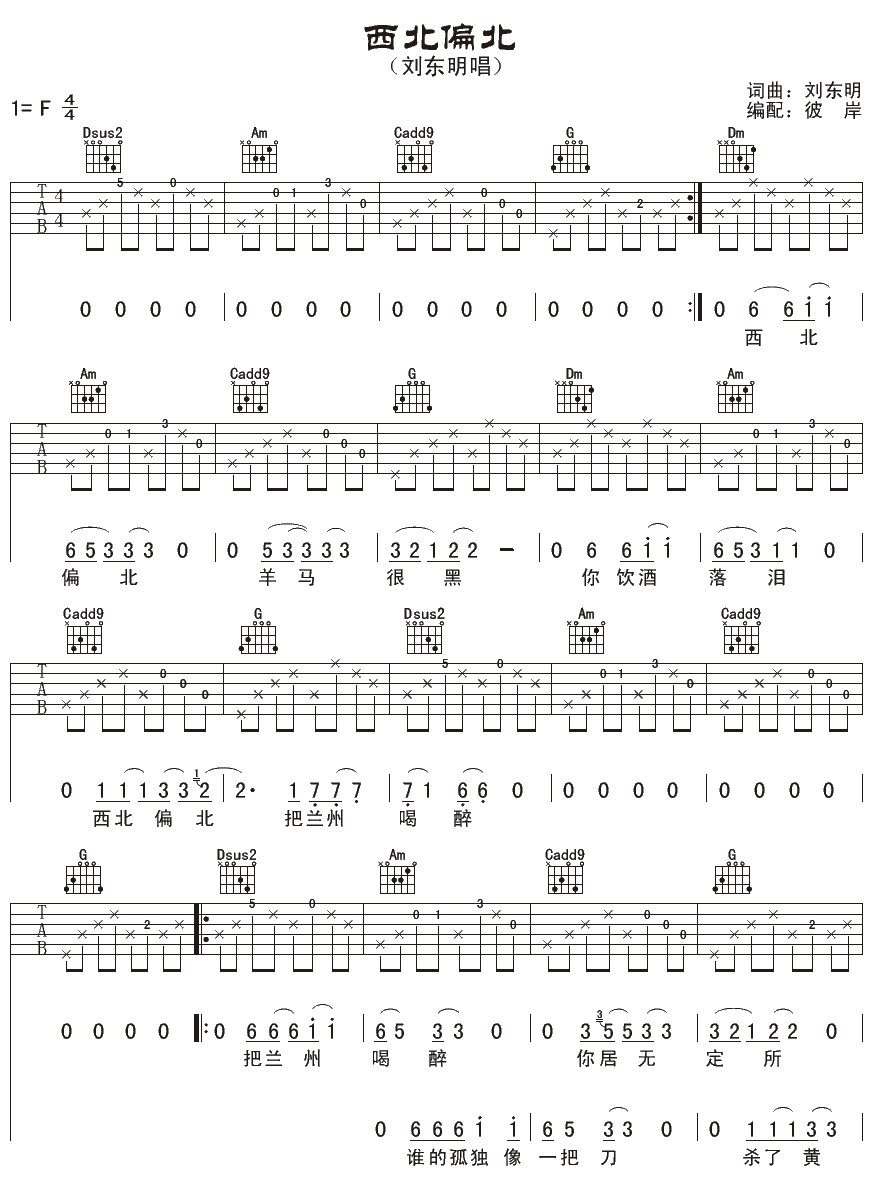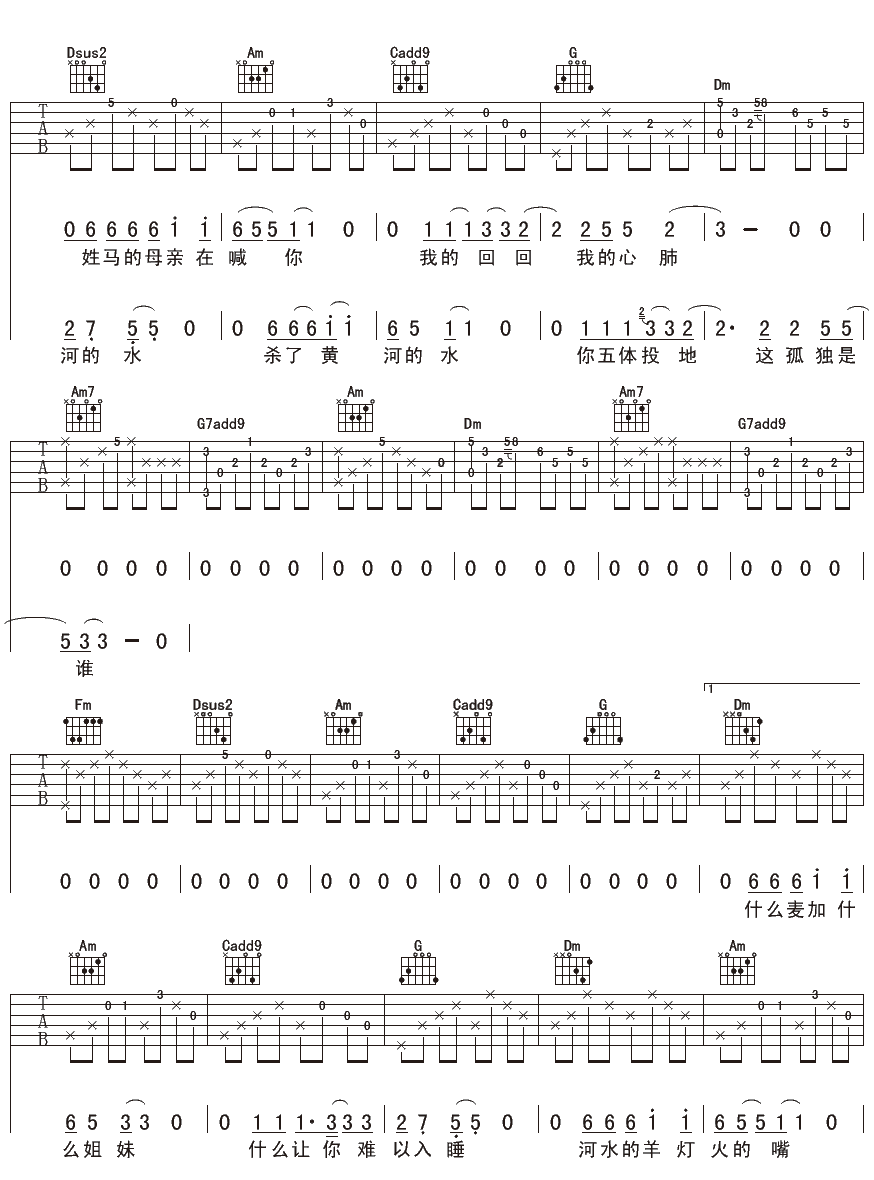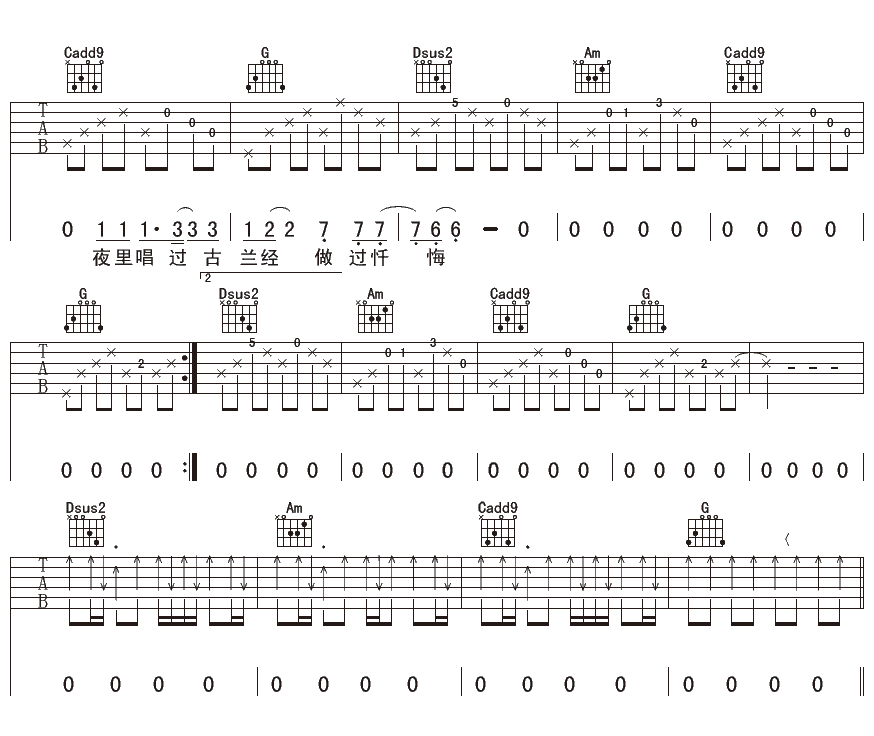《西北偏北》以粗粝苍凉的意象群构建出荒原般的精神图景,羊群啃食闪电的魔幻画面与黄河泥沙俱下的浑浊意象形成超现实张力。铁皮火车在戈壁腹地碾碎星光的场景,暗喻现代文明对原始诗意的野蛮入侵,而砂砾中发芽的格桑花则成为倔强生命力的图腾。歌词中反复出现的方位词构成空间迷局,西北偏北既是地理坐标更是精神荒原的隐喻,被酒精浸泡的指南针指向游牧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撕裂带。乌鸦衔着经幡飞越发电站的画面,浓缩了信仰与科技的永恒角力,而牧羊人手中锈蚀的转经筒,在柴油机轰鸣中保持沉默的旋转。所有意象最终坍缩成酒馆陶碗里的月亮倒影,倒映出正在消失的驼队剪影与拔地而起的水泥森林。这首歌词用意象的暴力嫁接完成对现代性侵袭的抵抗仪式,在语法断裂处暴露出土地与灵魂共同的伤口,那些未被驯服的野性在合成器音效与马头琴的混响中寻求和解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