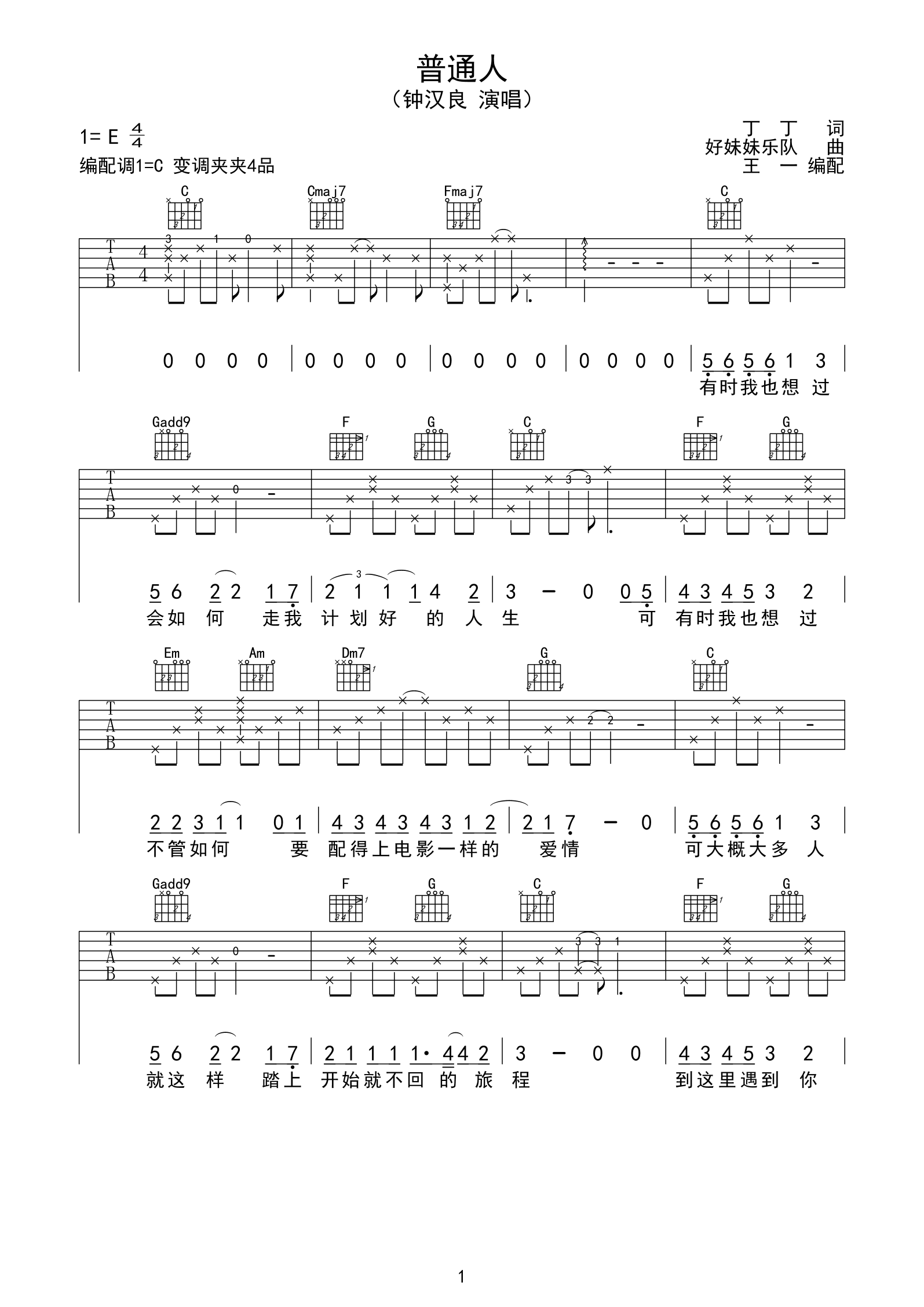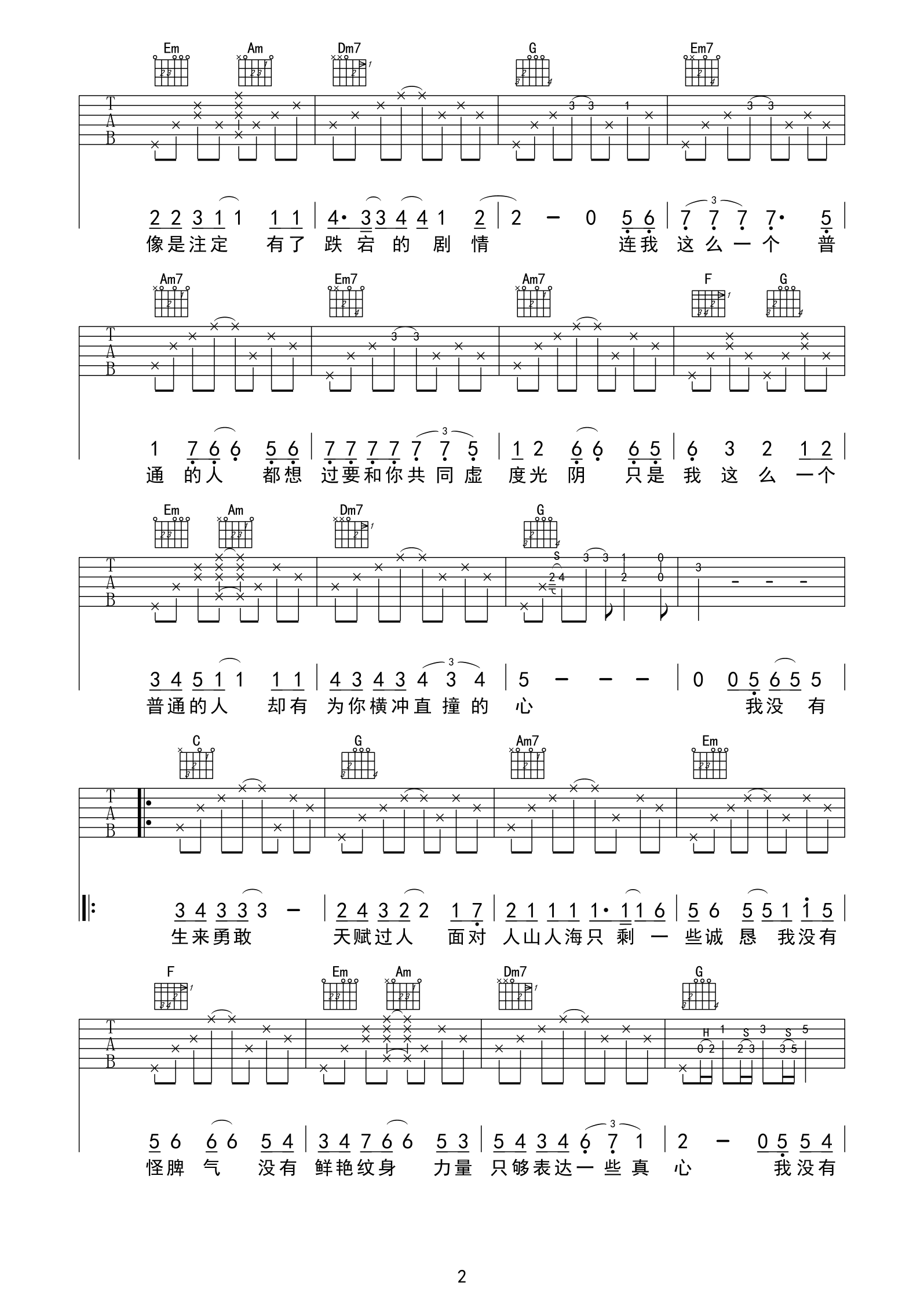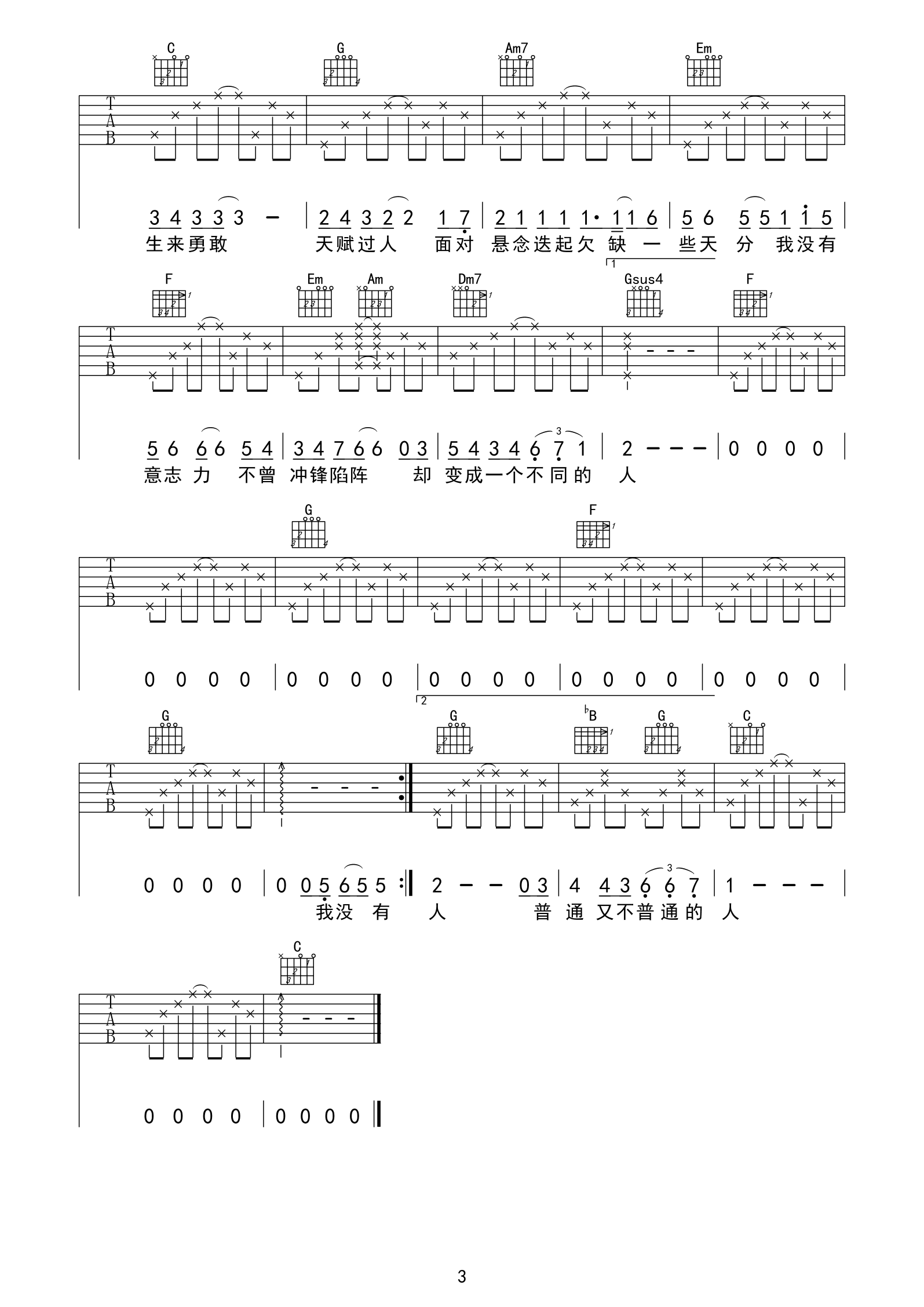《普通人》以平实克制的笔触描绘了都市生活中个体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困境,歌词通过具象的生活场景拼贴出当代人的精神图谱。早高峰地铁里的麻木面孔、深夜泡面升腾的热气、出租屋漏水天花板的意象群,共同构建了物质时代下的生存荒诞性。这些细节并非简单的现实主义描摹,而是通过重复出现的"普通"一词解构现代生活的标准化陷阱——当"普通"成为集体无意识的追求目标时,个体反而陷入更深的异化状态。副歌部分"用指纹解锁明天"的隐喻颇具后现代意味,生物识别技术作为数字时代的身份认证,在此转化为对存在确定性的质疑。歌词中反复出现的数字意象如"23:59的闹钟""15平米的星空",将时间与空间量化成可消费的单位,暗示着人被异化为资本逻辑中的计量符号。但作品并未停留于批判层面,"在水泥森林里开出花"的悖论式表达,既承认生存环境的坚硬质地,又保留了微小生命力的存在可能。这种矛盾修辞恰恰构成了当代普通人最真实的精神写照:在系统性的无力感中,仍保持着非英雄式的坚韧。歌词最终指向的是现代性困境中人的尊严问题——当"普通"成为时代病症时,承认并直面这种普通,反而可能成为抵抗异化的开端。